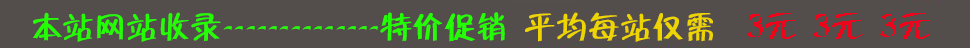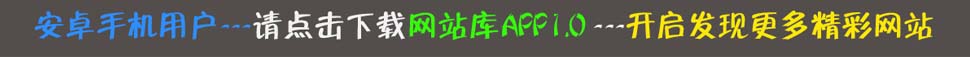2022年1月7日,李梁(化名)來到十薈團長沙辦公樓前,他想討回十薈團欠他的費用,共計50多萬元。但是這里已經人去樓空。李梁是長沙十薈團網格倉的經營商,他在2020年5月加入,手里有幾個長沙的網格倉。
1月14日,《財經》記者來到十薈團北京總部辦公室,辦公室里大部分工位都空著,一些辦公區域被雜物填滿,只有零星幾個人坐在辦公區域玩手機、聊天。一位自稱是十薈團的安保人員出面表示,他每天要接待十幾個上門來要錢的人,多的有幾百萬元,少的也有幾萬元。他還提到,十薈團還欠他所在的安保公司幾十萬元的費用。
十薈團北京辦公室的很多區域已經堆滿了雜物。拍攝/柳書琪十薈團北京辦公室的很多區域已經堆滿了雜物。拍攝/柳書琪
社區團購平臺十薈團成立于2018年8月,共完成了7輪融資,總融資金額超過10億美元。僅2020年就完成了4輪。阿里巴巴共參與投資了4輪,是十薈團的重要股東,也曾是合作伙伴。最新一輪融資是2021年3月完成了7.5億美元融資,由阿里巴巴領投,投資方還包括DST Global、晨曦投資、時代資本、GGV紀源資本、昆侖資本等多個知名投資機構。
和李梁一起去十薈團“討債”的有幾十個人,他告訴《財經》記者,他們大多都是湖南本地的網格倉經營商,還有一些是供應商,共計欠款超過1000萬元。網格倉是社區團購里的中轉倉,大倉將貨品運到網格倉后,再由網格倉進行最終環節的配送。李梁稱,從2021年9月起,就未收到十薈團應該付給他的配送費用。
他還提到,有其他人從6月開始就沒收到過錢了。
一位2021年7月從十薈團離職的員工告訴《財經》記者,他在十薈團完成最后一輪融資時加入,3個月后,公司就開始裁員,他和其他員工甚至一度懷疑這一輪融資的錢是否真的到賬了。
包括《財經天下》在內的多家媒體報道稱,十薈團裁員幅度驚人,從最高峰的超過1萬人,縮減到幾百人。《財經》記者多次致電十薈團CEO王鵬,電話被掛斷或無人接聽。
李梁回憶,在完成最后一輪融資后,十薈團立刻開始大幅補貼,希望通過燒錢來提高GMV(交易總額)和訂單量。GMV是互聯網行業最看重的指標之一,但這恰恰是讓十薈團走入困境的核心原因之一。
作為曾經風險投資市場熱捧的公司,還曾獲得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的大力支持,十薈團是怎樣一步步走入困境的?十薈團身上發生的很多事,不僅同樣發生在其他社區團購平臺上,還有不少類似模式的公司都遇到過。
爆雷
加入十薈團之前,李梁在經營一家菜鳥驛站,同樣是物流配送相關領域。2020年初,他周圍有很多人都在談論社區團購,也有不少人找他加入。
當時,社區團購平臺剛剛開始搶占市場,類似長沙這種二三線城市是它們的主要進攻方向。十薈團在長沙來勢洶洶,收購了長沙本地的幾家公司,并大力宣傳阿里是它們的投資方。李梁考慮,有阿里背書,這家公司應該會相對更有實力。
剛加入時,李梁手里的訂單少得可憐,只能自己跑市場、拉用戶。當時十薈團給他們承諾,每天至少保底700元——如果費用低于700元,都按700元算;如果高于700元,則按照實際支付。
對于網格倉來說,訂單量越高,均攤的配送成本就越低,大家都希望可以盡快提高單量。對于社區團購平臺來說,最快的方式就是低價補貼。李梁記得,每次融資后,十薈團都會進行一輪補貼,補貼力度驚人,本身價格已經很低的情況下,還有滿減券。
2021年上半年,十薈團的訂單量在補貼的助力下大增。李梁說,當時在長沙,十薈團的訂單量是美團買菜和多多買菜的兩倍以上,只低于起家于湖南本地的興盛優選。
2020年12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就已經出臺相關政策,要求社區團購不得低價傾銷。2021年3月,十薈團因“特價傾銷、擾亂市場秩序和以虛假手段誘騙消費者下單”,被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處以150萬元的頂格處罰。頂格處罰也未能阻止補貼的腳步,5月,十薈團又因同樣的原因被處罰50萬元。
從2021年6月以后,十薈團訂單量開始逐步下滑,越來越少。到了8月,李梁手里的兩個網格倉開始虧損。十薈團平臺的SKU(指最小存貨單位。 全稱為Stock Keeping Unit)逐步減少,從最高時2000多個,到300個,到現在不到100個。
十薈團的負責人告訴他,要么他交2萬元押金,要么就關倉。李梁隱隱覺得有些擔心,他沒有交押金,選擇關倉。關倉后的問題也來了,十薈團應該支付的費用一直未結清。
隨后,十薈團的相關人員一直勸李梁和其他網格倉負責人,轉型做2B業務,也就是批發給超市、餐廳。李梁沒有同意,費用一直收不到,他在12月時去了長沙十薈團的辦公樓,那時就已經人去樓空了。
李梁還需要支付配送司機們的工資,到了11月,他已經拿不出錢了,只能去貸款。12月,他連貸款都拿不到了,司機們向他討要薪資回家過年,甚至表示要堵在他家門口。
他說,跟他一起來討債的,有已經7個多月的孕婦,還有因為自己要去找新的工作不能來,只能讓家里70多歲的父母上門討債的。他們給之前聯系過的十薈團高管們打電話,CEO和董事長聯系不上,其他高管要么聯系不上,要么稱已經離職。
上門討債幾天后,十薈團外聘的律師帶來一個解決方案,要求他們簽訂協議,5個工作日后支付10%的欠款,3個月支付15%,隨后每個季度支付15%,直至付完。但李梁他們并未接受,“付我10%才5萬元,這筆錢根本無力支付司機的工資,而且他們沒有提供任何擔保,現在簽了大概率是拿不到后面的錢了。”
此時,討債人們想起了還有阿里巴巴,李梁和其他人也曾試圖去阿里巴巴討要說法,得到的回應是,阿里和十薈團已經沒有業務往來關系,只是投資方而已。
2021年8月,十薈團曾經發布內部信提到,正在與阿里巴巴MMC業務進行區域整合,資源互補、團隊協作。
2021年9月15日,十薈團宣布全面關停云南昆明的網格倉。隨后,十薈團廣州、福建、浙江等多個省份業務大范圍關停。
2022年1月3日,北京市朝陽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對十薈團處罰30萬元,原因是消費者下單付款成功后,十薈團未發貨,也未補發并取消訂單。
長沙的十薈團欠款事件甚至已經出現了一些過激行為。政府相關部門也已經出面維護秩序,但截至目前,這一問題仍未解決。
貓膩
2020年末,十薈團董事長陳郢發布內部信,信中提到,“對于十薈團的伙伴們來說,社區團購的意義超越了一個能賺很多很多錢的商業模式和創業項目(雖然我們確實也會賺很多很多錢)。”
2021年3月,十薈團拿到阿里領投的7.5億美元,彈藥充足,開始補貼。對于當時的十薈團來說,競爭極其激烈,滴滴、拼多多和美團都已經下場,巨頭們有更充足的資金和平臺效應,創業公司只能靠一輪又一輪的融資來維持燒錢。
想要繼續融資,就必須說服投資人,燒錢能換來顯著增長。這是持續了多年的互聯網行業發展主要邏輯之一。
李梁說,當時總部給各個區域下達指令,每個區域制定了明確的工作目標,要達到一定量的GMV。但是社區團購的每個城市、區域、網點的情況都不一樣,很難用同一套標準來要求。GMV是電商平臺慣用的數據口徑,指平臺上的成交金額,并不能和用戶數量直接掛鉤。
當時補貼的不僅是十薈團,幾乎所有的社區團購平臺都在補貼。低價并不足以堆出快速增長的GMV。
一些區域的業務員開始“刷單”。因為補貼力度足夠大,很多商品的價格低于成本價,不少相關業務人員會自己下單,然后轉手把這些商品賣給其他供應商,或是熟悉的小超市。甚至還有供應商會先給十薈團發貨,然后供應商再自己下單買回來。
李梁說,這些事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但沒人戳破。十薈團官網上明確指出,所有員工“不用職務之便,做有損公司利益的事;不得利用公司的商業秘密和所掌握的業務資源,聯合其他單位及個人參行牟利活動,或參與對公司構成潛在競爭的活動,包括但不限于向平臺團長兜售其他非平臺的商品,或以低于平臺的價格兜售平臺商品,通過套小號獲取雙重返利等。”
一位給多家社區團購平臺供貨的供應商告訴《財經》記者,這類現象并不僅發生在十薈團身上,其他社區團購平臺也有類似的情況。
不僅如此,在十薈團上還發生了一些讓李梁不能理解的現象,他發現,很多標品,例如礦泉水、可樂等,十薈團的進貨價甚至比其他平臺的零售價還要高。“我們有理由懷疑,十薈團內部出現了問題。”
讓李梁覺得內部有問題的不止這一件事。他說,另外一家也在長沙市場份額很高的社區團購平臺,會給每個網格倉配備一個業務經理,負責幫助網格倉解決問題。很多網格倉的運營商并沒有物流配送相關的經驗,網格倉的工作看似簡單——將商品配送到顧客手里,但實際操作中會遇到很多問題,例如時效性和成本的控制,用戶體驗的細節等。但在十薈團,是很多個網格倉配一個業務經理,經理只能每天巡視一遍,無法提供有效幫助。
內耗嚴重、不計后果的燒錢換訂單量、管理流程出現問題,十薈團面臨的壓力不僅是政策要求和行業競爭,更多的是自身出現了問題。
一位關注這一領域的投資人告訴《財經》記者,投資人在投資一個項目時,其實很難去一一核實這些細節問題,尤其是當這個項目很火時。他同時提到,“過去也有一些公司出現過類似的問題,但是隨著業務量的增長,慢慢地把這些漏洞都堵上了。”
但是,十薈團可能已經等不到堵上漏洞的時候了。
社區團購還有機會嗎?
2020年末的內部信中,陳郢提到,“社區團購打的是整個電商市場”,“整個中國的消費品市場(除房和車等固定資產性大額消費投入之外),都是我們的市場疆域——這是一個35萬億元的市場”,“社區團購能把一二線城市消費的同品質、同價格的消費品,直接供應到農村。至此,消費平權終于被實現,背后是無法估量的社會價值。”
社區團購業態于2018年出現,平臺將商品采購后,通過層層物流,配送至小區門口的取貨點。這一模式的好處是節約了生鮮電商很難降下成本的最后一公里配送環節,同時減少了一定的房租成本。疫情讓社區團購模式迎來爆發式增長,互聯網巨頭和資本立刻跟進。
對于互聯網巨頭來說,社區團購有利于帶來新的流量增長。因此不少互聯網公司都對社區團購提出“投入不設上限”的規劃。